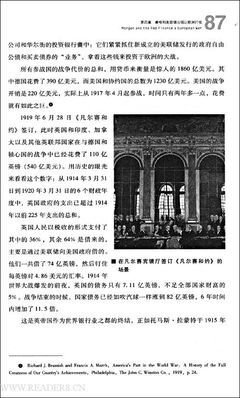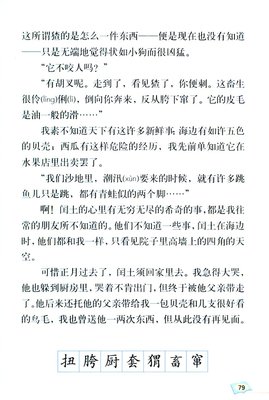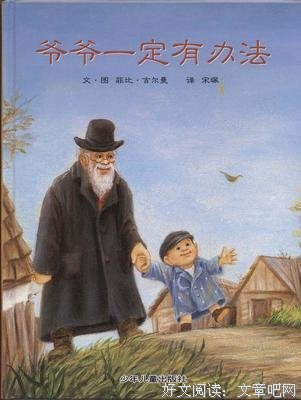《明清社会和礼仪》是一本由科大卫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一):明清社会与礼仪
本书论及的不是珠三角地区在明代之前是否有宗族组织的问题,而是在已有的家族形式下,宗族制的形式及正统礼仪普及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珠三角看到的所谓“传统”农村,实际上是明中叶嘉靖年间礼仪转型的结果。晚至宋代,珠三角大部分地区仍脱离国家管辖,国家力量仅延伸至广州等少量城市。官方把祭祀视为一种专利,祭祀前代贤吏视为一种官方的宗教活动,甚少宗族祭祀。明初,国家对珠三角实行里甲制。这是一个双互的过程,既是国家力量的进一步下渗,也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一种承认。至明嘉靖年间,大礼仪改变了有关祭祖和建立家庙的礼制规定,品官建庙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明中后期,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地税多于力役,不得不承认地方大族的权威。同时,黄箫养之乱和排佛运动也为异军突起的新兴地主阶层提供了契机,依靠中央可接受的理据,决定地方权益,逐步开启宗族的正统化。宗族渐成为社会核心,并演变成为田土开发的控制产权机构。这些机构控制田产和墟市,多姓共有的财产,以共同建庙的方法管理,合同隐藏在礼仪活动的演出中;单姓独有的财产,则按宗族的方法管理。可以发现,明中后期在里甲制的主导下,以地方与中央税收和财政的关系为核心,族谱、田产、拜祭的相互发展。
珠三角的士大夫成为治人者和治于人的中介,背后依靠的正是宗族力量。16-18世纪,地方群体最初以祭祀地点为核心建立起来,后转变为赋税登记的群体,再变为宗族。不过,祭祀地点的宗教礼仪和组织没有消失,转为以祠堂为核心的组织。另外,宗族具有弹性,共同的世系证明不是必要条件。依托宗族,可以提高社会地位,逃税,结盟等。同时,宗族内部的产权争执并不少见,积累起来的土地不是宗族所有,而是由个人或群体建立起庄园。
“中国”在不同时空的存在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根据采用朝廷认可礼仪的历史,可标志地方与朝廷的整合时间。福建地区在宋代即纳入国家体系。宋朝对福建地区采用地方神祗以遵行朝廷礼仪为中心的士大夫仪式,道统掌握在和尚和道士手中,把文书挪用于仪式上,渐用朝廷样式,实现地方领导力量和国家象征性整合。至明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福建宗族实质是加在一个现有神祗拜祭制度;其祭祀空间建于墓地,由僧侣看管,与祠堂分离,不建于村内。这两层的礼仪,皆混在同一个建筑物的标志里。至此,科大卫甚至猜测,福建莆田地区可能从来都不是以宗属为本,而是一个地域社群。
最后,文字传统和植根于非文字的社会风俗相结合,并重新呈现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族谱不只为了同样享有居住权的人,也为了那些只有在定期礼仪中才走在一起的人编撰。珠矶巷传说的多姓氏群体的源头,与这些群体的相互责任无关,但却关系到一个共同的背景,确立居住权的需要。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二):筆記
- 在學而優找到這本書。因工作關係, 有幸久不久去廣州學而優及北京萬聖書園走走, 總會有所得著, 包括這一本書.
- 這個新史學的系列, 最早讀到的是《再造病人》, 對當時的我打開了一片新天地。及後也有讀到梁其姿老師、楊念群老師的書, 所以也特別留意這一套系列。
- 科大衛與香港甚有淵源, 在香港生活與教書多年。可惜以前沒有留意, 也就沒有機會多認識了解。
- 這本書是本文集, 把科大衛過去的學術文章重新刊登, 大部份是原文是英文翻譯的作品, 也有少數是原來就以中文所寫的。書的最後有一個出版說明, 好像暗示部份文章版權可能會有爭議; 加之在後記中科大衛提到自己沒有閱讀翻譯的文章, 令人有點奇怪。
- 書名叫"明清社會和禮儀", 但其實多數文章談的年代, 更多是明初至明中的年代, 也有上溯宋元, 反而清朝的東西則不多。
- 作者本身是華南研究出身, 在改革開放以前主要透過香港新界的研究來了解傳統中國裡的社會。改革開放後, 他與其它學者(如蕭鳳霞)開始做珠三角的研究, 也開始接觸到福建莆田的研究, 將領域擴展至華南地區。再後來更涉足山西等地, "告別華南"。
- 書中收入的<告別華南研究>一文, 本身就用中文寫, 文字簡單易懂。該文清楚交代了他的研究進路, 包括從60年代起新一代中國研究學者如何嘗試擺脫上一代學者的理論框架, 從禮儀、宗族等角度嘗試去了解明朝以降國家與地方的關係, 對入門者如我來說是很好的介紹。
- 關於明朝的歷史脈絡, 我始終無法說得清楚。但作者經常會談到從明朝的里甲制過度至宗族/祀堂等經過, 有一個宋朝以來的理學背景, 也有在地社會與國家negotiate的過程, 也有"大禮儀"的爭論中廣東仕人的政治賭注等........... 其實十分有趣, 有心者自己找書來看好了.
- 書中提到很多東西之前都不大了解, 像甚麼鄉飲酒之禮, 甚麼道教科儀等, 令人慚愧. 科大衛早年很多研究是建基於香港的村落, 可惜的是這些知識大概已不為香港社會所知曉。當中提到宗族/倫學的道統與道教/喃嘸的關係, 沒有被朝庭認可的信仰 (如金花婆婆、其它更傳統的信仰等), 都很值得進一步去了解學習。
- 隨著政權的更替及現代化的歷程, 理學的道統與國家政權已不像明清時那樣緊緊走在一起(近年的國學熱是另一件事, 但放在幾百年的歷史裡或許也可讀出些甚麼), 但道教的傳統其實還是流行在香港乃至華南地區, 實在應該好好研究這一方面學香港/珠三角民俗的關係。
- 因為作者的框架甚清楚, 每篇文章大概都會說類似的東西, 所以讀到後來就有點悶了。
- 除了道教的東西外, 還很想找蕭鳳霞的書來讀讀。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三):对话科大卫 历史研究,不止于书斋 (新京报采访)
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发表《告别华南研究》,其中有个故事让不少学人动容。20世纪70年代,他曾经在罗湖、深圳交界的村庄中做口述采访,一个老婆婆讲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老婆婆一边讲一边哭,同行的同事一边听一边哭。那一刻,科大卫感到“有点愤怒”。“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我记得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
结合这个故事,科大卫在《明清社会和礼仪》的后记中的自白就更好理解。“我基本上是个历史学者(我的博士学位是修读社会学的),但是对人类学者的田野活动很有兴趣,也有幸得到人类学者朋友的指导与帮助。我并不相信我懂多少人类学,也对现在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追求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国社会史需要结合田野的观察与文献的解读。我相信不走出书斋的历史学者(借用贺喜的一句话)不能了解中国社会”。
从田野的角度读文献是科大卫倡导的研究方式。文献的内容是一层一层的,原来某句话经历过解读,又放了另一篇文献之内,如此转手多次,才到达历史学者的视野。而“我们这些城市长大,五谷不分的人”,要通过跑田野才可以有“看透文献的想象力”。
那么科大卫为我们呈现的中国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明清社会是何种样貌?明清地方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和人群,如何利用物质、符号手段,挤进已逐渐成形的政治制度,并安身立命其中?在《明清社会和礼仪》中,他客观地记录了同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建筑的特征等,并重构了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通过个案研究,科大卫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学界不少人将科大卫视为“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却认为从来没有什么“华南学派”,不故步自封,才能走得更远。与科大卫的对话启发我们,不要轻易地相信、想当然地引用一些概念和名词,它们都有特定的背景和生产的过程,当时当下合适,却不见得今时今日合适。做什么具体的研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直到看到真相,这也正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求真、客观。B02-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
新京报:你在一些文章中讨论到田野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每一座乡村里的老庙都是一本丰富的地方史,去庙里应该带着去图书馆、档案馆的心情。在华南跑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座庙是哪里?它最打动你之处是什么?
科大卫:很多庙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对我研究上最有冲击的是佛山的祖庙。可能因为我开始研究的时候,还没有预料地方宗教在一个市镇上有那么明显的标签作用。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社会的统一性源于共同的礼仪,这种共同并非中国各地全然一致,而是地方礼仪通过协调进入到中央认可的一套礼仪系统中,加固和延续社会的稳定。包括宋代的礼仪改革,目的是维持社会现状,而非推动社会革命。从思想认同具体化到地方实践的礼仪系统,对于中国明清社会稳定性的影响有多大?这种影响是否还表现在经济、思想等其他领域?
科大卫:要看“稳定性”是什么意思。从宋到清,中国地方上的礼仪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要不要以“革命”来形容只是一个文字上的问题。礼仪只是一种表现,假如你的“稳定性”是关乎权力或经济,我相信动力不是来自礼仪。
新京报:是否可以理解为:地方基于宗族的礼仪的前提,是国家基于皇权的一种映射。那么这套清明建立起来的礼仪系统受到的最大冲击,是来自于想要改变社会现状、质疑皇帝与国家关系的社会革命,如清末孙中山等人推动社会革命,以及1919年倡导“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
科大卫:宗族礼仪的前提,一定不是皇权而是祖先(宗族礼仪提倡拜祖先,不是拜皇帝)。皇权也接受宗族礼仪的时候,拜祖先为前提的活动可以应用到多方面,例如乡村组织,商业集资。五四运动反对旧礼教,也以为地方宗教是“迷信”,对宗族礼仪有些冲击。但是我并不相信“最大冲击”来自五四运动。我相信最大的冲击来自社会的改变:城市代替了乡村的政治地位、医药代替了传统神明、商业法律代替了传统的关系,等等。
新京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整合中,明清时期中国民间社会的独立性有多大?你更认同这种民间社会是一种智性的构建,而非一个有公共性的空间?所以,如果从明清社会的礼仪系统这一角度,要如何解释中国的民间社会在近代没有形成大家热议的“公共空间”?
科大卫:(1)“公共空间”是个以西方为核心的概念。它源于十八世纪欧洲反专制的言论。欧洲反专制,不只反对皇权独专,也反对专制的教会。中国没有统一的教会,所以,假如需要在中国应用“公共空间”的概念,不必把宗教排在其外。(2)同时,欧洲反专制的工具与中国也不一样。欧洲的思想,把秩序归根于法律。中国的思想传统,把秩序归根于“礼”。欧洲的法律,并不等同中国的“法”。所以,需要在中国应用“公共空间”的概念,当然可以包括礼仪传统下的民间社会。没有什么理由把民间社会与“公共空间”对立。
新京报:《告别华南研究》一文中,你谈到需要到华北去,走出华南研究的范畴才可以把中国历史写成是全中国的历史。研究华南的学术共同体被外界称“华南学派”,你怎么看这种叫法?
科大卫: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做学问需要思想开放,搞学派是自寻死路。
在科大卫看来,对宗族礼仪的“最大冲击”来自社会的改变:城市代替了乡村的政治地位、医药代替了传统神明、商业法律代替了传统的关系,等等。
什么历史令我们感觉是“普通人”?
新京报:今天大多数中国大众都觉得“天地会”是一个实际的实体,有一群密谋反清的兄弟在筹划。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认知又被金庸等作家的《鹿鼎记》及其改编的流行影视作品加强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描写清朝皇帝“出征平乱”的影视剧中。但实际上,你认为这些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的认同。
科大卫:正如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一样,也从来没有过天地会。生动的名词引起人们的幻想,但是幻想是否事实需要考证。
新京报: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传统中国”。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有个“传统中国”,可我们自己往往也不清楚“传统中国”到底从什么时候形成或是什么样子。但这种认同和建构有现实意义和功能,是国家和社会有意在营造的一种历史认同?
科大卫:中国有传统不等同中国只有一个传统,更不等同只有一个传统中国。不懂中国历史的人,例如研究当代的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不方便承认他(她)们不懂,所以把他(她)们不懂的中国称为“传统中国”。
新京报:是否可以把以上两个例子理解为精英想象的那种历史?你提到希望人们对于中国的理解更深刻,这就需要去超越精英想象的那种历史,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是值得倡导的一条路。
科大卫:我不是很相信社会由“精英”领导,所以也不是很相信有一个“精英想象的那种历史”去超越。我比较相信,因为权力和资源不是均等的,不同群体相信的历史在不同权力与资源下竞争。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对历史的信念都一定源于利己的阴谋。更大程度上,他们的信念来自缺乏考证。很多历史理念,好像“圣诞老人”一样,能维持下去,不是因为有历史的支持,而是符合信仰者的需求。
新京报:历史人类学如今已经走过了30年了,从“历史人类学”被学者构建出来,到历史人类学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接触到。对于未来三十年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你有哪些具体的期冀?
科大卫:“历史人类学”只是一个标签。我希望应用这个标签来刺激有些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思考。
新京报:历史人类学家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清深刻的历史,那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觉得我们要如何在社会、国家层层有意或无意的认同建构中,去把握个体对于历史的独立认知?
科大卫: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连“普通人”的概念也需要反思。“普通人”普通吗?我们经历了什么历史令我们感觉我们是“普通人”呢?从这里开始吧。
你的历史就是你
新京报:16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礼仪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按社会地位(里甲)登记的户口,迅速让位给明朝法律认可的“祠堂”,即以祭祖活动地点为中心的组织。对照当下中国的户籍制度来看非常有趣,因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一套严密的户口制度。你会怎么看当代中国户籍制度与里甲制的关联?
科大卫:里甲制度是一种户籍制度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明初的政府当然没有当代政府的行政能力,所以运行上有很大的区别。二者似乎都不是很能够在市场制度下延续。我怀疑在市场发达的环境运行身份制是很困难的。
新京报:你从一个很有趣的角度讨论过当代中国和历史的关联:“在经济和政治的范畴中,我还看到庇荫的结构无处不在,知识分子(请不要把我包括在内)跟过去的士子相差无几,清末以来对所谓”西方“又爱又恨的二元对立观延续至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里中产阶级物欲横流也许是乡村社会节日狂欢的替代品”。中国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确是很多人关注的,你如何想到从乡村社会节日狂欢来解读它?
科大卫:我研究的明清时代的乡村,没有电影、电视、手机、连收音机都没有。娱乐是需要由人直接提供的。那个时候的乡村也没有工厂生产的潮流衣着或依靠广告和超市引诱小孩子口味的糖果汽水。现在的城市人可以天天享受乡村的节日狂欢。但是节日还是多了参与,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维持节日,让大家在很商业化的环境下,参与消费。做生意的人,还是很明白消费者从历史遗留下来的习惯的。
新京报:为了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很多人在谈论什么是新的,而你希望展示的是:在今天中国的官僚制度、经济、宗教、文学、社会和其他方方面面,历史无处不在。所以在每天都在变的中国,当下中国社会如何处理与历史的关系,才是比较合理和理智的?
科大卫:如何处理才是理智的,不由我定。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可以说的,是不管你如何处理,历史不会跑掉。即使你想办法遗忘,它也在你的深处控制住你。历史不是在你以外的一个东西。你的历史就是你。
新京报:你谈到研究中国的历史,最终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从17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到现在,中国史一直很受西方学者关注。人们通过读中国史,可以对于世界史的了解增加哪些更深的认识?
科大卫: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世界史当然撇不开中国历史。当我们说要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好像已经有一套现成的世界史让我们放进去。但是,中国史还没有放进去的历史,并不是世界史。把中国史放进去的世界史,还需要我们的想象。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12/17/content_664416.htm?div=-1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四):谁来守候传统
争着抢着买这本书,亚马逊多次提醒库存紧张仍然坚持不退货,最终亚马逊客服受不了我的执着帮我查全国库存总算慢悠悠的到了我手里。科老师借这本相关文章合集集中探讨维持庞大帝国的乡村社会秩序的力量,如本书一直强调的16世纪以来的中国的礼仪、宗族建构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围绕“家庙”祭祀形成的地域性宗族成为维持乡村秩序的主体。关键词:礼仪革命、、礼仪领袖、控产机构。正如“历史阿牛”提出的:在科老师看来,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也许随着现代形式的移民流动,这400年来新发明的“传统”将逐渐真的变成传统了。祠堂、寺庙、仪式……都将无人守候。喜欢科老师后记里的一句话:“多少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认同。”历史学者和民俗学者果然是相同又不同,历史学者倾向于历时的追溯社会事实的脉络,民俗学倾向于系统的结构的共时研究,现象学的考察特定的社会事实产生的文化逻辑和精神互动的特殊形式。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五):如何走出华南
关于华南学派的诞生,学界一直流传着以下故事。1939年抗战正酣时,还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所任职的傅衣凌,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逃到城外十多里的一间老屋里。这间民房很早就被废弃,居民逃亡时带走了全部家当,唯独留下了一口大箱子。出于好奇,28岁的傅衣凌翻检它后,发现里面装的全是从明末到民国的契约文书,总计有上百张,包括田契、租佃契约和账簿等等。空袭警报解除后,他将这箱文书搬走,根据它们写成三篇文章,集结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成为华南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
我最早是在一堂讨论课上听到这段轶事,后来读中华书局版“傅衣凌著作集”,在前言里又多次重温,一开始深信不疑。后来才隐隐觉得,这个故事太过传奇,太过浪漫,以至于显得不那么真实。它与中国的传奇小说一样,似乎分享了某个同样的“母题”:懵懂无知的主人公因缘际会,误入深山,发现了失传多年的秘籍,此后不断钻研,终于成为某门派的开山祖师——发现契约箱的故事,太像是这类“母题”的变奏。
更重要的是,在介绍傅衣凌的学术生涯时,他1935至1937年间东渡日本,在法政大学攻读社会学的经历,往往被人们忽略了。要知道,早于傅氏三四十年前,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1875-1962)、南方熊楠(1867-1941)、折口信夫(1887-1953)等人,就已经开始利用口述、民间文书、歌谣等材料,来研究日本庶民的日常生活了,用日语来说,这是“常民”的历史。曾在日本学习的傅衣凌,不可能对这一潮流浑然不觉。
通常被认为是华南学派大将的科大卫(David Faure),在新书《明清社会和礼仪》中,也对这个故事提出了强烈质疑:“这是个牛顿和苹果的故事案例,只可能有一半真实性”,他判断道。因为在1939年时,民间土地契约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材料,“我们的乡土研究者中,家里有田地的也大有人在,有田地的人大概也有契约。为什么大家没有发现可以利用地契来写历史,而需要等到傅衣凌这个意外发现才联想到历史来呢?”另外,英、日等外国学者利用地契做中国史研究,也早于傅衣凌。
所以华南学派的真正开创性,并不在于新材料的发掘,以及田野调查方法的引进。若“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就能概括这个学派的话,那清代顾炎武、王昶、吴大澂等金石学者,或自骑毛驴寰宇访碑,或派拓工四出寻访,不也是在做田野么?所以科大卫才说:“问题不在于田野中有什么特别的资料去收集,问题在于怎样以田野的眼光读文献...用田野的角度读文献,文献的内容是一层一层的,原来这句话经历过解读,又放在了另一篇文献之内,如此转手多次,才能达到历史学者的视野。”
这段话多少有些晦涩难解。我个人揣摩科大卫的意思,就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关注文献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的,它在诞生之后,在不同时代又经过了哪些阐释、使用或曲解。如同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在到达不同地点时会有迥异的波幅一样,文献怎么“被理解”的历史,其重要性往往不亚于理解原作者的本意。
正是通过这种“田野的眼光”,华南学派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重塑了我们对于明清中国社会,尤其是宗族的看法。在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宗族被视为早已有之的“封建”余毒,它用“吃人的礼教”压抑个人、配合王朝专制,对于中国近代的落后要负主要的责任。但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科大卫的《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等著作却绕开了这一成见,指出在明清经济发展过程中,宗族是富有活力的一个组织单位。
至少在福建、广东地区,宗族不是古已有之的,是新生事物。科大卫认为,宗族社会“萌芽于16世纪,熬过了17世纪明清王朝交替的冲击,而终结于19世纪。”当它在18世纪如日中天时,未曾细究的人们“已把宗族视为古老的制度,而忘却了它的16世纪的根源。”要知道北宋末年,当广州知府蒋之奇到任,准备祭奠孔子之时,却发现当地的儒学只是一所简陋的窄堂:“在北宋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佛寺都要比儒学更宏伟体面。”
珠三角文士传统的崛起,是从元代开始的。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明朝后,其政权的残酷性,其实超过了元末。新政权承袭前代,以职业划分户口,在民户中广泛推行里甲制,铁腕地对基层社会进行重编。只不过这种一里十甲、一甲十户,由里长、甲首带领民户轮流承担国家的赋役的制度,究竟如何执行至今还不明了。《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里只有些简略的记载,各地方志说法不一,后来虽经过梁方仲、王毓铨等人的苦心研究,学界仍然莫衷一是。
很遗憾,科大卫对里甲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只是认为它在珠三角执行得并不彻底:“不过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地域社群保留了他们的权力结构。”但在前著《皇帝和祖宗》里,他却又曾说过推行里甲制度“影响当地的权力分配”,在珠三角地区“凡编入里甲者,其田产将得到王朝国家的承认,亦即得到王朝国家的保护”,那些最积极配合的民户,就成了珠江三角洲上最有势力的陆上宗族。里甲到底是促进了宗族的产生,还是对之无太大影响?科大卫的前后表述不一,颇令人困惑。
不论如何,在16世纪的嘉靖时代,华南地区的商业化过程继续塑造着宗族。科大卫认为,除了民间经济的力量以外,明世宗上台后,为了尊称亲生父亲为王而在朝臣中引发的“大礼议”,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北京官员分裂为两派,广东籍士大夫霍韬、方献夫、湛若水三人,均支持新任皇帝,就这样“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潮流,与王朝中央的潮流汇合起来。”其标志是1525年,霍韬回到家乡,新建了“可能是珠江三角洲第一座公开兴建的‘家庙’式祠堂。”
建立家庙式祠堂的构想,最早来自南宋大儒朱熹。借助“大礼议”的波澜,这一构想开始走出书斋,进入民间基层社会的运行之中。明中期以后,华南宗族通过编纂家谱、建造祠堂的方式,将个别成员所获得的功名,转化为宗族整体的“象征资本”。同时,有力的宗族还兴办族内教育,帮助子孙获得功名;辟出族田,赈济族内贫弱孤寡;出现纠纷时,宗族内部还有一套调解机制,无需求助官府。这时候的大宗族功能越来越完备,几乎可以自给自足。
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man)用corporation来称呼这一时期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宗族。科大卫盛赞道,这一概念“为华南社会的研究指引了新方向。”但为corporation寻找一恰当的中文词汇却有些困难。在《皇帝和祖宗》里,卜永坚将其译为“法人”;《明清社会和礼仪》则时而译为“控产机构”,时而又维持“法人”的原译。但两种翻译,皆无法完全传达其原意:宗族作为一个集体,有明确的成员制度,并能够拥有财产,能否加入它,不取决于血缘关系,而取决于能否追溯至同一个祖先,“以姓氏来建立的联盟,就是宗族”。
华南宗族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沙田开发。由于耗资巨大,这项活动必须由若干大家族联合进行。珠江三角洲的大姓,像番禺何氏、三江赵氏、顺德罗氏等,大多是通过投资沙田而积累财富,扩张势力的。宗族成员的科举功名也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建立与地方官府的良好关系。就这样,宗族与宗族间的差距被不断拉大。所以说与欧洲不同,珠三角的阶级鸿沟,并不存在于士农工商之间,而存在于以姓氏建立起来的各个联盟之间。
这就是为什么,科大卫称赞弗里德曼“控产机构”概念“不但发现了华南乡村生活的根本结构,也发现了产权维持和资金汇集相结合的原则。”社会史与商业史因而被打通了。宗族对外追求经济利益,对内则实行轮流管理制,将所得利润用于族内事务,“管理权和产业利润均沾权相结合,保证了共同拥有原则的落实。”只要利益一致,追溯共同祖先的工作总有办法解决,通过编族谱、建祠堂的方式,“同族同宗”就被逆向建构了。
所以明清时候的宗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僵化保守,固执地维持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原始状态。相反,宗族灵活地适应着经济的变化。在这一方面,福建与广东的情况非常类似。郑振满曾指出,福建的宗族分为以血缘为基础的“继承式家族”、以地缘为基础的“依附式家族”、以利益为基础的“合同式家族”三种。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时间的胶着状态中,“男子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家立业,维持一定规模的大家庭,以利于改善家庭经济结构”,通过内部分工,宗族往往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
那么,明清中国北方有没有类似珠三角、长三角那样的大宗族呢?科大卫肯定地回答,宗族原则对于华北地区的社会组织也很重要,“一姓村显而易见是主导”。具体来说,尽管华北的宗族没有祠堂,但直到现在,华北仍然保留着在墙上贴写有祖先名字的纸张,定期祭祀的习惯。尤其山西南部的阳城县、襄汾县、夏县,其宏伟的家族聚落,无不体现出宗族力量的强大。
但华南学派的这一着“北进”,步伐甚为勉强。首先,科大卫书中提到的北方宗族,基本都是山西地区的票号世家,样本的同质性太强。但山西票号的核心业务,乃是为皇室提供金融服务,此乃明清经济史的常识。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是绝不可能在整个北方广泛推行的。但与人口稀疏、以小农为主的北方不同,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光是海外与中国内陆之间的贸易,便足以支撑起千千万万个大宗族了。更不要说南方的土地一年多熟,租赁过程中有复杂的“一田多主”现象,根据傅衣凌、黄宗智、曹树基等人的研究,其田地权的转移已经有了股票的雏形,这些都是北方所不具备的。
虽然地理决定论不可取,但明清华南宗族的形成,不仅仅是个历史现象,亦是气候、地理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缺乏环境史视角的情况下,仅选取几个个案,贸然用类比和套用,便说“一姓村显而易见是主导”,恐怕是有欠推敲的。
我们往往会被“中国”这个词的大一统性所迷惑,以自己地方化的经验为基础,试图推及全国。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不正如此吗?这些生长于浙闽粤沿海宗族势力最强地区、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们,发表太多“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西方是动的文明,中国是静的文明”之类似是而非的言论。重要的不是将华南学派的结论移植北方,而是继续用“田野的眼光”,揭示中国内部的异质性。
(已经发表于第792期《经济观察报》,转载请征求作者或报社同意。)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六):“礼仪革命”造成的“传统社会”
也许,我们今天认知中的“传统社会”只有400年历史。科大卫教授的研究聚焦于早期近代中国的礼仪、宗族,以及商业,处理如此复杂议题的十几篇文章,今年以《明清社会和礼仪》的题目编集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这些精彩的研究也许会概念有关“传统社会”的“常识”。
贯穿科大卫教授丰富研究的问题是:维持如此庞大帝国的乡村社会秩序的力量是什么?这个提问来自20世纪中叶西方学界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三种不同观点。第一,认为社会的秩序来自政府控制。第二,认为士绅阶层与朝廷合作,造成了一种社会秩序。第三,认为16世纪以来的中国出现了“公民社会”。
科大卫认为以上三种解释各有缺陷。以萧公权先生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认为政府的控制带来了社会秩序,但是,他又同时将有秩序的社会定义为受到控制的社会。这其实变成了一个循环论证。如果认为士绅阶层连接起了国家与社会,那么首先需要质疑的是,是否存在一个利益一致的士绅阶层?至于“公民社会”,这本是一个从近代西方历史的世俗化进程中归纳出的概念,但世俗化恰恰不能概括早期近代中国的历史特征。
那么,16世纪以来的中国是否经历了一场社会结构的转变呢?如果转变曾经发生,真正根本性的特征是什么?科大卫教授给出的答案是:礼仪。
礼仪如何为早期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向心力与秩序?宋元之际与明初的若干变化至关重要。首先,文字书写在乡村中更为普及,将文字带入乡村的,不仅有儒家的教书先生,也有在乡村中主持各种仪式、祭祀的仪式专家。当文字传播开后,人们不仅运用文字书写祭祀神灵的仪式,或者与朝廷权威息息相关的各种儒家伦理,同样也用于书写土地契约、账簿、家谱等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书。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16世纪,宣称信奉儒家礼仪的宗族建设及祭祖仪式越来越普及。科大卫教授对此的研究重点是珠江三角洲。宋元之际以及明初,广州城之外的珠江三角洲对于朝廷来说,尚属荒凉之区。但在16世纪,这里出现了霍韬这样介入“大礼仪”的朝廷重臣,也出现了陈白沙这样的理学领袖。从陈白沙到霍韬,他们都在积极建设朱熹《家礼》中提倡的宗族礼仪。围绕“家庙”祭祀形成的地域性宗族成为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主体。
在科大卫看来,上述的宗族建设与“礼仪革命”不仅仅是珠三角的区域变化。16世纪整个中国都在经历这场变革。从福建到山西,建设祠堂都是16世纪乡村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特征。
“聚族而居”也许在后人看来是中国传统乡村的主要面貌。但宗族与乡村社会的紧密结合,可能主要是16世纪以来的历史产物。更重要的是,与一般印象不同,“聚族而居”造成的并非自给自足的、封闭的乡村经济,恰恰促动了更为开放与流动的商业发展。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将华南乡村中的宗族称为“控产机构”(corporation),英语里,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公司”。科大卫评价说“他不但发现了华南乡村生活的根本结构,也发现了产权维持和资金汇集相结合的原则。”(12页)
明清以来商业的发展,并非跳出王朝所认可的身份,而是利用这些身份。士绅、宗族,常常与商人是一体两面。披上士绅、宗族身份的商人们所建设的市镇,可能从两个方面击破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常识”。
第一种“常识”,是马克思·韦伯所认为的,传统中国的城市、民间社会毫无独立于皇权政治之外的力量。城市仅仅是行政中心,商人们仅仅是依附于皇权与官僚。明清时代作为行政中心的省城、府城、县城之外,尚存在大量的市镇。这些有时规模超过“万户”的市镇中,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官僚寥寥无几,甚至不存在,但商人们以宗族或士绅的名义修建祠堂、庙宇、会馆,主导了绝大部分地方事务。这些“礼仪领袖”比起韦伯假设的私人提供的社群服务,角色更为重要。(231页)
第二种“常识”,是将市镇中宗族、士绅、商人的活动,视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社会”的崛起。不论哪一个概念,对于16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是不恰当的比附。“中国的镇的资产阶级虽则是资产阶级,却并不冲击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131页)佛山这样的超大型市镇的早期历史,是围绕庙宇祭祀形成的乡村联盟。但当市镇吸引了更多外来移民,也由于经济发展与税收的原因引起官府注意时,较早获得科举成功的士绅们开始领导市镇中的事务。他们也将市镇中人群、资源的聚集中心从寺庙转变为祠堂、义学、义仓,从而为官府所接受。这样,商人在市镇中构建起了适合他们的社会秩序,同时却并未突破他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身份、位置。
科大卫教授将宗族与礼仪视作16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核心,也许刘志伟老师十几年前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制度史方面的回应:“明清里甲制下`户'的性质的衍变,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是建立在土地财产和对民间社会组织的从属关系的基础指望,而不像过去的传统那样建立在编户齐民对王朝的直接人身隶属关系之上。在这样一种与以往的传统不同的社会秩序下,民间社会必然与国家权力在政治上和利益上趋于一致,处在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中介的作用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既然`户'本身并不是一定的社会实体,而是一定的课税客体或税额的登记单位,那么共同支配和使用同一`户头'的社会成员之间,必然形成某种形式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就成为单个社会成员与官府之间最为基本的中介。……因此,图甲制下的`户'的构成及其变动,实际上是清代宗族组织分化和重组的一种折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204页)
刘志伟老师的焦点是赋役制度中“户”的意义,似乎与科大卫教授所谈的“宗族”、“礼仪”无涉。但赋役制度中“户”的意义发生变化,乡村社会中原本的社会组织形态就会以新的“户”的形式进入官府的登记。宗族建设,正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另一面。
礼仪革命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的不是某个区域的地方社会,而是试图理解什么是明代的中国,或什么是清代的中国。(37页)在我理解,科大卫教授心目中好的历史叙述,应当包含那些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而非宏大事件的组合。科大卫教授2004年所发表的《告别华南研究》中有一个我始终动容的故事。他谈到20世纪70年代曾经在罗湖/深圳交界的村庄中做口述采访,一个老婆婆讲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老婆婆一边讲一边哭,同行的同事一边听一边哭。那一刻,科大卫教授的感受是“有点愤怒”。在他看来“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我记得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198页)
也许,随着现代形式的移民流动,这些400年来新造成的“传统”将逐渐真的变成传统了。祠堂、寺庙、仪式……都将无人守护。我来自东北一个典型的工业移民城市,那里没有祠堂、寺庙,甚至没有家谱,这里的地域人群组织方式,以及“控产机构”都与宗族无关。前几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朋友抱怨:楼下的祠堂清早六点作仪式,真是太吵了,祖上中过进士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一位地道的闽南人,来自科老师所描述的那种16世纪以来的礼仪传统的核心区。但是新的一代,已经未必都能认同这种礼仪传统了。
我在朋友圈里对那位朋友说,如果是我们这些历史学者,听到仪式锣鼓声的第一反应,只怕是兴奋地爬起床过去围观。不过,这可能更多出于专业兴趣,并不意味对此有任何思古之幽情,或今不如昔之感,但也更不会目其为所谓“落后、封闭”的东西而欲其速死。历史是冷峻的。如同科老师在后记中所说的:多少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认同。随着人群的变动,认同也在变,这是无可如何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只是理解这些变化,令曾经“没有历史的人”能够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声音。
(原文发表于澎湃新闻,2016年11月26日)
附勘误:
75页,引《广东通志》:殊不知五岳惟五万诸侯得以祭之。
可能应为“五方诸侯”。
80页,引《重修曹溪通志》:调太常寺少卿,致事家富。惟一子,已爱而夭,无嗣闻其后也有悔于心。
疑应为:调太常寺卿,致仕。家富,惟一子,已爱而夭,无嗣。闻其后也有悔于心。
http://m.sbbzjw.com/gandongwenzhang/238224.html
推荐访问:社会礼仪教案